10_29_2005課程
第四節 音樂
浪漫主義派(Romantic)
代表性人物
舒伯特(F. Schubert, 1797-1828)、韋伯(C. Webber, 1786-1826)、孟德爾頌(F. Mendelssohn, 1809-1947 )、蕭邦(F. Chopin, 1810-1849)、舒曼(R. Schumann, 1810-1856)、白遼士(H. Berlioz, 1803-1869)等。
浪漫主義派特色
浪漫主義派的標記是需要台詞對白或詩的歌劇。在初期是以歌曲作為與古典主義的分野;浪漫主義不只在音樂方面,同時在造形藝術以及當時的文學均密切的聯繫。在
音樂本質上浪漫主義派是強調個性、作者主觀,打破傳統形式的。
音樂的形式上以交響曲為首的器樂以及使用海頓所確立的奏鳴曲形式。
音樂的內容則從 古典的、文靜的,漸次移轉成動態的情緒抒發。
古典的、文靜的,漸次移轉成動態的情緒抒發。
浪漫主義派的精神在舒曼、蕭邦、白遼士等人達到極點:舒曼藉著歌曲、鋼琴曲表現夢想及文學、蕭邦將內藏的熱情及敏銳熟練的感情轉換為鋼琴曲,白遼士則直率地表現出個人的體驗及主觀。在浪漫主義時代最盛行的音樂也可說是浪漫主義導火線的是歌曲與歌劇,初期的歌曲之王舒伯特擅長將詩與音樂完全混成一體,提高了歌曲的藝術性。歌劇先驅德國人韋伯創作的特色是:用歌劇表現出德國傳統的民族性以及故事,同時大量採用戲劇性的要素(左圖為韋伯之歌劇-魔彈射手);而他的同胞華格納(R. Wagner, 1813-1883右上圖)更將歌劇視為一項綜合的舞台藝術,表演者與管絃樂團同樣地受到重視,過去以優美旋律為中心的現象均已消失,代之而起者為壓倒性的說服力,戲劇感強烈地逼迫聽眾(觀眾)。
民族樂派(Ethnic)
簡述:
浪漫樂派在基本上是個性的自覺,也就是一種解放的音樂,並不普遍地追求理想,而是對自己忠實,由此而表現出作品的結晶,因為每一個音樂家自身的血統不同,若忠實於自己的作品,當然就產生民族性風格。民族樂派是以浪漫樂派為基礎延續發展而來,浪漫樂派的作曲家中,韋伯、蕭邦、李斯特、華格納等人,不論其有無意識,在其作品中皆可嗅出相當濃厚的民族味道;古典至浪漫樂派時期,音樂的主流在德國,但是19世紀後半,各國各自走出德國的掌握,而樹立各自的風格。
印象主義派(Impressionism)
簡述:
印象主義音樂產生於十九世紀末,是受“象徵主義文學”和“印象主義繪畫”的影響而出現的一種音樂流派。這一流派的音樂家與此前的浪漫主義音樂家有很大區別,他們並不通過音樂來直接描繪實際生活中的圖畫,而更多的是描寫那些圖畫給我們的感覺或印象,渲染出神秘朦朧、若隱若現的氣氛和色調。法國人德布西和拉威爾兩位音樂家,是集印象主義音樂之大成者。印象主義音樂是浪漫主義音樂向現代音樂過渡的橋樑之一,雖然這一樂派主要集中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法國,但這種風格對於近現代音樂的發展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現代樂派(Modern)
在每個國家,本世紀的作曲家們都在對音樂的諸要素——如節奏、旋律、和聲、曲式——進行著實驗。在此除了在上週提出一些實驗音樂的範例之外,不多贅述。以下僅針對人所熟知的爵士音樂做一概略說明:在本世紀所有基於民族和社會習俗的音樂中,沒有哪 一種比(美國)爵士音樂具有更廣泛的影響力(右圖為美國知名爵士樂手Louis Armstrong)。由於爵士音樂狂熱的節奏和古怪的不協和音,從某方面講,它似乎是新時代的一種表現。爵士音樂有許多對職業音樂家們產生吸引力的特色,(例如其中帶有小三度和小七度的音階,以及基於小三度和小七度音階的七和絃等等)。可是,最具強烈感染力的爵士音樂特色,是它那獨具特色的節奏。在爵士音樂裏,同時有兩種很強烈的節奏型相互對立,(例如一個三拍子節奏加在一個四拍子節奏上)。這種錯綜複雜的多重節奏顯然是原始民族的音樂特點,因此爵士音樂的興起,無疑是人類對於自然的一種理性回歸,這是本世紀各種藝術形式的共同趨向之一。職業的音樂家們也被那些不常使用樂譜的、甚至事實上常常不會讀譜的原始爵士音樂演員們所迷住。在一時的衝動之下,這些自發的爵士音樂演員可能在一個旋律上即興演奏出最複雜的變奏曲。
一種比(美國)爵士音樂具有更廣泛的影響力(右圖為美國知名爵士樂手Louis Armstrong)。由於爵士音樂狂熱的節奏和古怪的不協和音,從某方面講,它似乎是新時代的一種表現。爵士音樂有許多對職業音樂家們產生吸引力的特色,(例如其中帶有小三度和小七度的音階,以及基於小三度和小七度音階的七和絃等等)。可是,最具強烈感染力的爵士音樂特色,是它那獨具特色的節奏。在爵士音樂裏,同時有兩種很強烈的節奏型相互對立,(例如一個三拍子節奏加在一個四拍子節奏上)。這種錯綜複雜的多重節奏顯然是原始民族的音樂特點,因此爵士音樂的興起,無疑是人類對於自然的一種理性回歸,這是本世紀各種藝術形式的共同趨向之一。職業的音樂家們也被那些不常使用樂譜的、甚至事實上常常不會讀譜的原始爵士音樂演員們所迷住。在一時的衝動之下,這些自發的爵士音樂演員可能在一個旋律上即興演奏出最複雜的變奏曲。
附錄一
管絃樂配置圖基本上分為弦樂(Strings)、銅管(Brass)、木管(Wood Winds)以及打擊(Percussion)四個部份
附錄二
我摘錄了一篇有關於音樂欣賞的文章,已由簡體字轉為繁體字,請各位同學參考,原作者於音樂這一門表演藝術有非常有趣的描寫與觀點。摘錄自http://www.myscore.org/yuelun.htm
賞樂雜談
文: 阿鏜

一
內容與形式及技法的統一,是藝術作品成功的第一要素。莫札特(左圖)音樂和聲的清麗、透明,配器的單純、簡潔,與其內容的天真、高貴,有內在的因果關係。華格納音樂和聲對位元的複雜、豐富、多變,配器的宏大,厚重,與其內容的英雄性,所表現人性的矛盾及複雜性,也同樣是互為因果。類似莫札特的內容而用華格納的技法,類似華格納的內容而用莫札特的技法;非莫札特、華格納的內容而用莫札特、華格納的技法,都是東施效顰,愚不可及,絕無成功之理。
二
邊聽蕭斯塔可維奇的第十一交響樂,邊看金庸的武俠小說“天龍八部”,真是一奇特的享受。蕭氏與金庸,似乎在不同時空,用不同媒體,在說同一樣事情。小說主角蕭峰的悲涼身世,悲劇故事,與蕭氏的音樂處處吻合;蕭氏音樂中的悲哀、怨憤、殺伐之氣,以及那種他人所無的排山倒海衝擊力,處處可在小說中找到印證。有點可惜的是老蕭給他的音樂加了個大煞風景的標題。如蕭氏仍在世,當建議他把標題拿掉。
三
貝多芬是英雄,蕭斯塔可維奇也是英雄。莫札特不是英雄,是天使,是神仙。貝氏和蕭氏的音樂是入世的。莫札特的音樂是出世的。在蕭氏的音樂中,找不到莫札特那種天使般的單純、柔美;在莫札特的音樂中,也找不到蕭氏那種人生百態,特別是那種滿腹牢騷,憤世嫉俗。
四
反復聽蕭氏的第一、第五、第十一交響樂,覺得他的音樂有幾個顯著特點:1大——氣勢大、結構大、變化幅度大。2對位特別豐富——與二流作曲家如阿鏜等相比。3偏重內心描寫——與偏重外景外物描寫的作曲家如德彪西、史特拉文斯基等相比。4喜歡把弦、木、銅三組樂器當作三件樂器來使用,效果甚佳。不喜歡他的是常有尖銳、刺耳的不雅之聲。五 蕭氏十八歲寫成的第一交響樂,已達令人百聽不厭之境。如果“就文學來說,莎士比亞是上天給英國最厚的賞賜;就詩而言,杜甫是上天給中國最厚的賞賜”(黃國彬語,見“中國三大詩人新論”);那麼,就音樂而論,蕭氏大概是上天給俄國的最厚賞賜了。
六
對位功夫就像武功中的內功、內力。內力高強之人,任何招式使出來,都威力強大;缺乏內功之人,再高明的招式到了手裏都會變成花拳繡腳,中看不中用。
九
華格納與史特拉文斯基這兩位管弦樂法的頂尖高手,究竟誰更高段?論奇詭變幻,史氏無人可比。論氣魄雄渾,華氏更勝一籌。華氏的音樂“人”味多些,是正中見奇。史氏的音樂,“野”味多些,是奇中見正。如以此把華氏排在史氏之前,不知史氏在天之靈服氣否?
十
把馬勒和拉威樂的管弦樂作品比較一下,可得出這樣的結論:馬勒是結構派,線條派;拉威爾是色彩派,音響效果派。馬勒的作品,把其配器改變一下,當然其色彩會跟著改變,但其總的音樂效果仍然成立,不會大變。拉威爾的作品,則絕不能改動其配器。如把其所使用的樂器改變一下,不但會面目全非,連能否奏得出來都是問題。從整個管弦樂歷史來看,巴赫、貝多芬、布拉姆斯都可歸為結構派;勃遼茲、裏姆斯基.柯薩柯夫、德彪西、史特拉文斯基可歸為色彩派。華格納則是介乎兩派之間,兼具兩派之長的人物。
十一
拉威爾的“小丑的晨歌”一曲,聽鋼琴原作,不大聽得出味道,聽其管弦樂改編曲,則有如看光彩奪目的奇珍異寶展覽,每一句,每一個音都充滿奪人心魄的奇光異彩。有人用獨奏樂器的語言寫管弦樂曲,有人用管弦樂曲的語言寫獨奏曲,拉威爾無疑是後者。
十二
拉威爾的“波麗露”,固然是配器的典範之作,同時也是旋律、節奏的典範之作。如果沒有那樣一段色彩和節奏均變化多端,令人百聽不厭、百聽不明(如不是看著譜硬背,相信一般人聽上一百次也無法準確地把譜記出來)的旋律,單憑在配器和聲上變換花樣,該曲不會如此精彩。
十三
理查.史特勞斯的作品,譜上複雜、音符很多,但效果常不大出得來。他喜用快速、短音、高音,跟華格納正好相反。華氏喜用慢速、長音、低音。以招式的變化論,也許二人不分高下。如以招式的威力論,則華氏遙遙領先,非史氏可比。
十五
聽史特拉文斯基的“火鳥”和“春之祭”,深覺史氏真是不世出的奇才。難到極點,新到極點,效果好到極點的招式,在他手裏使出來,就好像流水從高處向低處流一樣自然、容易。對庸才如阿鏜者來說,連模仿他,偷學他的東西,都極不容易呢!
十六
史氏的“火鳥”全曲原譜與組曲曲譜,在配器和記譜上都有不少不同之處。此事至少說明一點:史氏創作精益求精,一改再改,絕不輕易放過任何可以改得更合理、更完美之處。真是“那裏有天才”之又一例證。
十七
對著總譜細聽亨德爾的“彌賽亞”,完全服了。其音樂精神的向上,對位元的巧妙,結構的精密,內涵的充實,素材的簡煉,恐怕三百年後的今人,也沒有一個能寫得出來。難怪有人悲觀地斷定,時至今日,古典音樂在創作上已難有作為,能有作為的只有唱奏和欣賞。
十八
聽巴赫的“馬太受難樂”和“B小調彌撒曲”,覺得巴赫的音樂無疑比亨德爾的音樂更嚴謹、更複雜、更精妙,但旋律卻不及亨的優美、活潑、雅俗共賞。也許,巴赫比亨德爾更神聖,亨德爾卻比巴哈更易令人親近。
二十
一般歌曲,是一段定江山——只要有一段寫得精彩,整首歌就立得住。可是賦格曲,卻是一句定江山——整首曲子,都是根據這一句衍生、發展、變化出來。如這一句立不住,整首曲子也就立不住了。如此說來,賦格曲固然在技巧上是登峰造極的形式,可是,“智”的成份往往多於“心”的成份,所以不容易為一般人所接受,以至逐漸式微。這種對格律的要求比我國的七言律詩還要嚴格的形式,只有在少數幾位真正大師手裏,才能成為心、智、情、理兼具的樂苑奇葩。
二十二
布拉姆茲的德國安魂曲,美到了極點。用這樣美的音樂來悼念、陪伴死者,真是人類文明登峰造極的表現。比起中國傳統追悼死者的恐怖氣氛和淒厲哭聲來,文明太多了。
二十三
常聽到“流行歌曲與藝術歌曲的分別在那裏”一類問題,甚至聽到“藝術歌曲應向流行歌曲靠近、學習”一類建議。其實,只要把常用來形容好的藝術歌曲之詞語,如“崇高”、“高貴”、“深厚”、“震撼人心”等,與常用來形容好的流行歌曲之詞語,如“夠勁”、“好甜”、“有磁性”、“一聽就會唱”等加以比較,便可明白二者之分別。至於二者是否應該和能夠互相靠近、溶合,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人都有兩面,一面是動物性的,如食、色、玩樂;另一面是精神性的,如宗教、文化、倫理。一萬年後,二者還是會並存,決不會合二為一。
二十四
人有人的語言,動物有動物的語言,繪畫有繪畫的語言,舞蹈有舞蹈的語言。管弦樂,也有管弦樂的語言。何謂“管弦樂語言”?此問甚難答,近于“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之類。然而,也非絕對不可答。以一句一段來說,能用人聲唱出來,或能用一件單音樂器奏出來的,一般都不是管弦樂語言,而是歌曲或某件獨奏樂器的語言。單件樂器奏來如拆碎之七寶樓臺,不成片斷,數件或全部樂器總合奏出來才完美無缺的,便是管弦樂語言。連續較長時間使用同樣樂器或樂器組合的,一般不是管弦樂語言;較頻繁地變換樂器或樂器組合的,是管弦樂語言。很容易改編成鋼琴譜,可以在鋼琴上完整無缺地彈奏出來的,一般不是管弦樂語言;很難改編成鋼琴譜,不大可能在鋼琴上完整無缺地彈奏出來的,是管弦樂語言。

二十五
以管弦樂語言的豐富來為古今中外的管弦樂曲排名次,史特拉文斯基(左圖)的“火鳥”第一。為方便分類、歸納、記憶、學習,筆者曾借用中國武術招式名稱,給華格納、拉威爾、史特拉文斯基等管弦樂大師的各種技巧、手法命名。結果發現,在同一作品內,論招式之豐富、多變、奇詭、險絕,史氏之“火鳥”比較他人之作品,不但遙遙領先,連他本人的其他作品也沒有一首能及得上。
二十六 “火鳥”中的招式,簡略列舉如下(括弧內之號碼為組曲譜之編號):此起彼落(2),長中有短(3),震音碎音(3),變化琶音(5),群雞啄米(9),重重疊疊(10),爬上爬下(12),機槍連發(13),撥弦敲弦(26),珠前線後(34),前呼後應(39),以靜襯動(62),縱橫交錯(69),舊酒新瓶(69至80),群雄助威(89),拆碎樓臺(93),緊拉慢唱(96),馬不停蹄(98),接力賽跑(104)。此外,在全曲原譜中才有的招式及不必舉例的招式尚有:鼓聲掀浪,群獸怒吼,剛柔相濟,一花獨放,好事成雙......等等。可惜筆者拙于文才,不能像金庸寫武俠小說一樣,給這些技法想出更美更准更絕的名稱,乃一憾事。
火鳥download欣賞 最後一首 firebird bercuese and finale
二十七
華格納的“尼貝龍指環”套歌劇之管弦樂片斷,有些史氏所無招式:水銀瀉地,四管齊鳴,以高伴低,弦木伴銅,你問我答,不分彼此,千軍萬馬,一統天下。有興趣研究者宜自己去找“那裏是那裏”,此處恕不公開“謎底”。
二十八
史氏“春之祭”的管弦樂法,最特出的一招是把整個樂隊當作一件打擊樂器來使用。以此招表現原始、粗野,不可謂不成功。可是,這實在是險到極點,近乎旁門左道的招式,稍為拿捏不准,便會“未傷敵而先傷已”。後來一些無此功力又無此內涵的東施之輩,濫用此招,把樂壇弄得一片剌耳鬼叫之聲,想這並不是史氏所樂於見到之事吧?
二十九
“用非管弦樂語言寫管弦樂樂曲”,例子可舉舒伯特為“露莎孟德”所寫的芭蕾音樂。雖然該曲充滿旋律美,句句可唱,但是,缺少對位,缺少戲劇性,缺少強烈的色彩變化和織體變化,從頭至尾只是旋律加伴奏,而且主要旋律都是頗為呆板的歌謠式節奏。以管弦樂曲論,這當然不算成功之作。請讀者勿誤會庸才阿鏜居然敢大貶天才舒伯特。以作品的充滿靈性、詩意、旋律和聲的美而自然、多變論,舒伯特是無人可及的。缺少第一流的對位技術而被公認為第一流作曲家,古今中外只有一位舒伯特。他三十一歲便英年早逝,可是給人類的音樂寶庫留下了多少無價珍寶!阿鏜對他連崇拜、欣賞、可惜都來不及,怎敢亂貶?怎忍亂貶?想指出的僅是:如缺少足夠的技藝與功力(包括對所寫之形式的瞭解和掌握),天才如舒伯特也會有不成功之作。凡夫俗子如我輩,欲寫好一曲半曲,能馬虎乎?能偷懶乎?能騙人乎?
三十
欣賞音樂難不難?說不難,何以鐘子期一死,俞伯牙便從此不再撫琴?可見知音不易得,賞樂相當難。說難,則何以除聾啞之人,生平不喜歡任何音樂,不曾自己哼唱過幾句的人幾乎找不到?可見音樂人人都能賞,絕非貴族之專利品。結論是:不同的人欣賞不同的音樂,不同的音樂需要不同的人來欣賞。欲賞樂者,不能不先弄清楚,自己是何種人,宜賞何種樂;欲人賞樂者,也要先弄清楚,自己有的是何種音樂,需要何種人才宜欣賞。如此,則不會有人埋怨欲賞無樂,有人埋怨有樂無人賞。
三十一
所謂“”知音難求,是指確實優秀,卻尚無人知的作家作品,不易遇到能賞識的人。時至今日,誰不會說“巴赫偉大”、“我喜歡貝多芬”?可是,偉大的巴哈去世後,整整一百年默默無聞,直到孟德爾松歷盡艱辛,把他的“馬太受難樂”排演出來後,世人才知道有巴哈。如問巴哈的在天之靈:“千萬世人尊稱您為音樂之父,究竟誰是你的真正知音?”大概巴哈會毫不考慮地答:“孟德爾松!”
三十二
賞樂如賞詩、賞畫,以“耐”字為高。詩要耐吟、畫要耐看、樂要耐聽。把柴可夫斯基和西貝柳斯的小提琴協奏曲相比較,相信一般人初聽都會喜歡柴多於西。可是聽到十次二十次以上,情形就很可能反過來,品位較高者會覺得柴協“膩”,西協卻越聽越有味。以此斷高下,自然是西高於柴。
三十三
如追根究底下去,是什麼因素造成一件作品“耐”或“不耐”?這是極難答的問題。就音樂來說,一般情形是厚重、含蓄,抒內心之情的作品比輕巧、華麗,描寫外界景物的作品耐聽;對位元豐富的作品比對位元貧乏的作品耐聽。但也不儘然。莫札特的作品並不厚重,舒伯特的作品對位元並不豐富,史特拉文斯基的作品以描寫外界景物的居多,但都很耐聽。無可爭議的是:情深情真的作品一定比情淺情假的作品耐聽。
三十四
中國傳統音樂與西方古典音樂的同異之處何在?同者,都講求好聽、高雅、有意境。異者,一、中樂音階一般是五至九聲,西樂音階是七至十二聲。三、中樂一般不轉調,西樂大量轉調。四、中樂器高音強低音弱,各種樂器的音色不易溶為一團,西樂器高中低音較平衡,大多數樂器的音色可溶為一體。五、中樂創作的思維一般是“砌磚式”,即越加越高,越加越長;西樂創作思維一般是“細胞分裂式”,即越變越多,越變越長。由此看來,西方古典音樂是已高而不易再高,中國傳統音樂是不高而大有機會再高。
三十七
論音樂充滿剛陽氣,古今中外,無人可與貝多芬相比。貝多芬的作品,充滿力感,永遠激勵人向上。有句話說:“學琴的孩子不會變壞”,也許還可以這麼說:“愛聽貝多芬音樂的人不會頹唐不振。”
三十八
每次聽貝多芬第九交響樂第四樂章,都有把靈魂清洗了一遍和跟最好的老師上了一堂作曲課的感覺。這真是一首神聖、神奇、集大成的至尊之作——一般人都能接受和喜歡它簡單、易唱、好聽的主題旋律;行家不能不佩服它極其高明的作曲技巧;政治家可從中體會出人類最崇高、最終極的政治理念;宗教家會認同其眾生平等,人類互愛,神偉大,人渺小的精神;哲學家會發現它用最抽象而直接的語言,把他們用長篇大論都講不清楚的意思和道理,全明明白白地講了出來;建築師和數學家會驚歎其總體結構的龐大精妙,每一個組成部分都互相關聯而經得起嚴格分析、計算;文人雅士可從中引發諸多聯想甚至由此產生新的創作靈感......假如世界上只准留下一首樂曲,其他統統不准存在(當然包括筆者敝帚自珍的數十首小作品在內),別無選擇,我只好略帶痛苦地把這一票投給貝多芬這首“歡樂頌”。
三十九
選詞作曲——詞長不如詞短,情短不如情長。
四十
賞樂三部曲——一、多聽,二、多聽,三、還是多聽。多聽自能出味道,多聽自能辨高低,多聽自然成樂迷。
第四節 音樂
浪漫主義派(Romantic)
代表性人物
舒伯特(F. Schubert, 1797-1828)、韋伯(C. Webber, 1786-1826)、孟德爾頌(F. Mendelssohn, 1809-1947 )、蕭邦(F. Chopin, 1810-1849)、舒曼(R. Schumann, 1810-1856)、白遼士(H. Berlioz, 1803-1869)等。
浪漫主義派特色
浪漫主義派的標記是需要台詞對白或詩的歌劇。在初期是以歌曲作為與古典主義的分野;浪漫主義不只在音樂方面,同時在造形藝術以及當時的文學均密切的聯繫。在
音樂本質上浪漫主義派是強調個性、作者主觀,打破傳統形式的。
音樂的形式上以交響曲為首的器樂以及使用海頓所確立的奏鳴曲形式。

音樂的內容則從
 古典的、文靜的,漸次移轉成動態的情緒抒發。
古典的、文靜的,漸次移轉成動態的情緒抒發。浪漫主義派的精神在舒曼、蕭邦、白遼士等人達到極點:舒曼藉著歌曲、鋼琴曲表現夢想及文學、蕭邦將內藏的熱情及敏銳熟練的感情轉換為鋼琴曲,白遼士則直率地表現出個人的體驗及主觀。在浪漫主義時代最盛行的音樂也可說是浪漫主義導火線的是歌曲與歌劇,初期的歌曲之王舒伯特擅長將詩與音樂完全混成一體,提高了歌曲的藝術性。歌劇先驅德國人韋伯創作的特色是:用歌劇表現出德國傳統的民族性以及故事,同時大量採用戲劇性的要素(左圖為韋伯之歌劇-魔彈射手);而他的同胞華格納(R. Wagner, 1813-1883右上圖)更將歌劇視為一項綜合的舞台藝術,表演者與管絃樂團同樣地受到重視,過去以優美旋律為中心的現象均已消失,代之而起者為壓倒性的說服力,戲劇感強烈地逼迫聽眾(觀眾)。
民族樂派(Ethnic)
簡述:
浪漫樂派在基本上是個性的自覺,也就是一種解放的音樂,並不普遍地追求理想,而是對自己忠實,由此而表現出作品的結晶,因為每一個音樂家自身的血統不同,若忠實於自己的作品,當然就產生民族性風格。民族樂派是以浪漫樂派為基礎延續發展而來,浪漫樂派的作曲家中,韋伯、蕭邦、李斯特、華格納等人,不論其有無意識,在其作品中皆可嗅出相當濃厚的民族味道;古典至浪漫樂派時期,音樂的主流在德國,但是19世紀後半,各國各自走出德國的掌握,而樹立各自的風格。
印象主義派(Impressionism)
簡述:
印象主義音樂產生於十九世紀末,是受“象徵主義文學”和“印象主義繪畫”的影響而出現的一種音樂流派。這一流派的音樂家與此前的浪漫主義音樂家有很大區別,他們並不通過音樂來直接描繪實際生活中的圖畫,而更多的是描寫那些圖畫給我們的感覺或印象,渲染出神秘朦朧、若隱若現的氣氛和色調。法國人德布西和拉威爾兩位音樂家,是集印象主義音樂之大成者。印象主義音樂是浪漫主義音樂向現代音樂過渡的橋樑之一,雖然這一樂派主要集中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法國,但這種風格對於近現代音樂的發展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現代樂派(Modern)
在每個國家,本世紀的作曲家們都在對音樂的諸要素——如節奏、旋律、和聲、曲式——進行著實驗。在此除了在上週提出一些實驗音樂的範例之外,不多贅述。以下僅針對人所熟知的爵士音樂做一概略說明:在本世紀所有基於民族和社會習俗的音樂中,沒有哪
 一種比(美國)爵士音樂具有更廣泛的影響力(右圖為美國知名爵士樂手Louis Armstrong)。由於爵士音樂狂熱的節奏和古怪的不協和音,從某方面講,它似乎是新時代的一種表現。爵士音樂有許多對職業音樂家們產生吸引力的特色,(例如其中帶有小三度和小七度的音階,以及基於小三度和小七度音階的七和絃等等)。可是,最具強烈感染力的爵士音樂特色,是它那獨具特色的節奏。在爵士音樂裏,同時有兩種很強烈的節奏型相互對立,(例如一個三拍子節奏加在一個四拍子節奏上)。這種錯綜複雜的多重節奏顯然是原始民族的音樂特點,因此爵士音樂的興起,無疑是人類對於自然的一種理性回歸,這是本世紀各種藝術形式的共同趨向之一。職業的音樂家們也被那些不常使用樂譜的、甚至事實上常常不會讀譜的原始爵士音樂演員們所迷住。在一時的衝動之下,這些自發的爵士音樂演員可能在一個旋律上即興演奏出最複雜的變奏曲。
一種比(美國)爵士音樂具有更廣泛的影響力(右圖為美國知名爵士樂手Louis Armstrong)。由於爵士音樂狂熱的節奏和古怪的不協和音,從某方面講,它似乎是新時代的一種表現。爵士音樂有許多對職業音樂家們產生吸引力的特色,(例如其中帶有小三度和小七度的音階,以及基於小三度和小七度音階的七和絃等等)。可是,最具強烈感染力的爵士音樂特色,是它那獨具特色的節奏。在爵士音樂裏,同時有兩種很強烈的節奏型相互對立,(例如一個三拍子節奏加在一個四拍子節奏上)。這種錯綜複雜的多重節奏顯然是原始民族的音樂特點,因此爵士音樂的興起,無疑是人類對於自然的一種理性回歸,這是本世紀各種藝術形式的共同趨向之一。職業的音樂家們也被那些不常使用樂譜的、甚至事實上常常不會讀譜的原始爵士音樂演員們所迷住。在一時的衝動之下,這些自發的爵士音樂演員可能在一個旋律上即興演奏出最複雜的變奏曲。附錄一
管絃樂配置圖基本上分為弦樂(Strings)、銅管(Brass)、木管(Wood Winds)以及打擊(Percussion)四個部份

附錄二
我摘錄了一篇有關於音樂欣賞的文章,已由簡體字轉為繁體字,請各位同學參考,原作者於音樂這一門表演藝術有非常有趣的描寫與觀點。摘錄自http://www.myscore.org/yuelun.htm
賞樂雜談
文: 阿鏜

一
內容與形式及技法的統一,是藝術作品成功的第一要素。莫札特(左圖)音樂和聲的清麗、透明,配器的單純、簡潔,與其內容的天真、高貴,有內在的因果關係。華格納音樂和聲對位元的複雜、豐富、多變,配器的宏大,厚重,與其內容的英雄性,所表現人性的矛盾及複雜性,也同樣是互為因果。類似莫札特的內容而用華格納的技法,類似華格納的內容而用莫札特的技法;非莫札特、華格納的內容而用莫札特、華格納的技法,都是東施效顰,愚不可及,絕無成功之理。
二
邊聽蕭斯塔可維奇的第十一交響樂,邊看金庸的武俠小說“天龍八部”,真是一奇特的享受。蕭氏與金庸,似乎在不同時空,用不同媒體,在說同一樣事情。小說主角蕭峰的悲涼身世,悲劇故事,與蕭氏的音樂處處吻合;蕭氏音樂中的悲哀、怨憤、殺伐之氣,以及那種他人所無的排山倒海衝擊力,處處可在小說中找到印證。有點可惜的是老蕭給他的音樂加了個大煞風景的標題。如蕭氏仍在世,當建議他把標題拿掉。
三
貝多芬是英雄,蕭斯塔可維奇也是英雄。莫札特不是英雄,是天使,是神仙。貝氏和蕭氏的音樂是入世的。莫札特的音樂是出世的。在蕭氏的音樂中,找不到莫札特那種天使般的單純、柔美;在莫札特的音樂中,也找不到蕭氏那種人生百態,特別是那種滿腹牢騷,憤世嫉俗。
四
反復聽蕭氏的第一、第五、第十一交響樂,覺得他的音樂有幾個顯著特點:1大——氣勢大、結構大、變化幅度大。2對位特別豐富——與二流作曲家如阿鏜等相比。3偏重內心描寫——與偏重外景外物描寫的作曲家如德彪西、史特拉文斯基等相比。4喜歡把弦、木、銅三組樂器當作三件樂器來使用,效果甚佳。不喜歡他的是常有尖銳、刺耳的不雅之聲。五 蕭氏十八歲寫成的第一交響樂,已達令人百聽不厭之境。如果“就文學來說,莎士比亞是上天給英國最厚的賞賜;就詩而言,杜甫是上天給中國最厚的賞賜”(黃國彬語,見“中國三大詩人新論”);那麼,就音樂而論,蕭氏大概是上天給俄國的最厚賞賜了。
六
對位功夫就像武功中的內功、內力。內力高強之人,任何招式使出來,都威力強大;缺乏內功之人,再高明的招式到了手裏都會變成花拳繡腳,中看不中用。
九
華格納與史特拉文斯基這兩位管弦樂法的頂尖高手,究竟誰更高段?論奇詭變幻,史氏無人可比。論氣魄雄渾,華氏更勝一籌。華氏的音樂“人”味多些,是正中見奇。史氏的音樂,“野”味多些,是奇中見正。如以此把華氏排在史氏之前,不知史氏在天之靈服氣否?
十
把馬勒和拉威樂的管弦樂作品比較一下,可得出這樣的結論:馬勒是結構派,線條派;拉威爾是色彩派,音響效果派。馬勒的作品,把其配器改變一下,當然其色彩會跟著改變,但其總的音樂效果仍然成立,不會大變。拉威爾的作品,則絕不能改動其配器。如把其所使用的樂器改變一下,不但會面目全非,連能否奏得出來都是問題。從整個管弦樂歷史來看,巴赫、貝多芬、布拉姆斯都可歸為結構派;勃遼茲、裏姆斯基.柯薩柯夫、德彪西、史特拉文斯基可歸為色彩派。華格納則是介乎兩派之間,兼具兩派之長的人物。
十一
拉威爾的“小丑的晨歌”一曲,聽鋼琴原作,不大聽得出味道,聽其管弦樂改編曲,則有如看光彩奪目的奇珍異寶展覽,每一句,每一個音都充滿奪人心魄的奇光異彩。有人用獨奏樂器的語言寫管弦樂曲,有人用管弦樂曲的語言寫獨奏曲,拉威爾無疑是後者。
十二
拉威爾的“波麗露”,固然是配器的典範之作,同時也是旋律、節奏的典範之作。如果沒有那樣一段色彩和節奏均變化多端,令人百聽不厭、百聽不明(如不是看著譜硬背,相信一般人聽上一百次也無法準確地把譜記出來)的旋律,單憑在配器和聲上變換花樣,該曲不會如此精彩。
十三
理查.史特勞斯的作品,譜上複雜、音符很多,但效果常不大出得來。他喜用快速、短音、高音,跟華格納正好相反。華氏喜用慢速、長音、低音。以招式的變化論,也許二人不分高下。如以招式的威力論,則華氏遙遙領先,非史氏可比。
十五
聽史特拉文斯基的“火鳥”和“春之祭”,深覺史氏真是不世出的奇才。難到極點,新到極點,效果好到極點的招式,在他手裏使出來,就好像流水從高處向低處流一樣自然、容易。對庸才如阿鏜者來說,連模仿他,偷學他的東西,都極不容易呢!
十六
史氏的“火鳥”全曲原譜與組曲曲譜,在配器和記譜上都有不少不同之處。此事至少說明一點:史氏創作精益求精,一改再改,絕不輕易放過任何可以改得更合理、更完美之處。真是“那裏有天才”之又一例證。
十七
對著總譜細聽亨德爾的“彌賽亞”,完全服了。其音樂精神的向上,對位元的巧妙,結構的精密,內涵的充實,素材的簡煉,恐怕三百年後的今人,也沒有一個能寫得出來。難怪有人悲觀地斷定,時至今日,古典音樂在創作上已難有作為,能有作為的只有唱奏和欣賞。
十八
聽巴赫的“馬太受難樂”和“B小調彌撒曲”,覺得巴赫的音樂無疑比亨德爾的音樂更嚴謹、更複雜、更精妙,但旋律卻不及亨的優美、活潑、雅俗共賞。也許,巴赫比亨德爾更神聖,亨德爾卻比巴哈更易令人親近。
二十
一般歌曲,是一段定江山——只要有一段寫得精彩,整首歌就立得住。可是賦格曲,卻是一句定江山——整首曲子,都是根據這一句衍生、發展、變化出來。如這一句立不住,整首曲子也就立不住了。如此說來,賦格曲固然在技巧上是登峰造極的形式,可是,“智”的成份往往多於“心”的成份,所以不容易為一般人所接受,以至逐漸式微。這種對格律的要求比我國的七言律詩還要嚴格的形式,只有在少數幾位真正大師手裏,才能成為心、智、情、理兼具的樂苑奇葩。
二十二
布拉姆茲的德國安魂曲,美到了極點。用這樣美的音樂來悼念、陪伴死者,真是人類文明登峰造極的表現。比起中國傳統追悼死者的恐怖氣氛和淒厲哭聲來,文明太多了。
二十三
常聽到“流行歌曲與藝術歌曲的分別在那裏”一類問題,甚至聽到“藝術歌曲應向流行歌曲靠近、學習”一類建議。其實,只要把常用來形容好的藝術歌曲之詞語,如“崇高”、“高貴”、“深厚”、“震撼人心”等,與常用來形容好的流行歌曲之詞語,如“夠勁”、“好甜”、“有磁性”、“一聽就會唱”等加以比較,便可明白二者之分別。至於二者是否應該和能夠互相靠近、溶合,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人都有兩面,一面是動物性的,如食、色、玩樂;另一面是精神性的,如宗教、文化、倫理。一萬年後,二者還是會並存,決不會合二為一。
二十四
人有人的語言,動物有動物的語言,繪畫有繪畫的語言,舞蹈有舞蹈的語言。管弦樂,也有管弦樂的語言。何謂“管弦樂語言”?此問甚難答,近于“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之類。然而,也非絕對不可答。以一句一段來說,能用人聲唱出來,或能用一件單音樂器奏出來的,一般都不是管弦樂語言,而是歌曲或某件獨奏樂器的語言。單件樂器奏來如拆碎之七寶樓臺,不成片斷,數件或全部樂器總合奏出來才完美無缺的,便是管弦樂語言。連續較長時間使用同樣樂器或樂器組合的,一般不是管弦樂語言;較頻繁地變換樂器或樂器組合的,是管弦樂語言。很容易改編成鋼琴譜,可以在鋼琴上完整無缺地彈奏出來的,一般不是管弦樂語言;很難改編成鋼琴譜,不大可能在鋼琴上完整無缺地彈奏出來的,是管弦樂語言。

二十五
以管弦樂語言的豐富來為古今中外的管弦樂曲排名次,史特拉文斯基(左圖)的“火鳥”第一。為方便分類、歸納、記憶、學習,筆者曾借用中國武術招式名稱,給華格納、拉威爾、史特拉文斯基等管弦樂大師的各種技巧、手法命名。結果發現,在同一作品內,論招式之豐富、多變、奇詭、險絕,史氏之“火鳥”比較他人之作品,不但遙遙領先,連他本人的其他作品也沒有一首能及得上。
二十六 “火鳥”中的招式,簡略列舉如下(括弧內之號碼為組曲譜之編號):此起彼落(2),長中有短(3),震音碎音(3),變化琶音(5),群雞啄米(9),重重疊疊(10),爬上爬下(12),機槍連發(13),撥弦敲弦(26),珠前線後(34),前呼後應(39),以靜襯動(62),縱橫交錯(69),舊酒新瓶(69至80),群雄助威(89),拆碎樓臺(93),緊拉慢唱(96),馬不停蹄(98),接力賽跑(104)。此外,在全曲原譜中才有的招式及不必舉例的招式尚有:鼓聲掀浪,群獸怒吼,剛柔相濟,一花獨放,好事成雙......等等。可惜筆者拙于文才,不能像金庸寫武俠小說一樣,給這些技法想出更美更准更絕的名稱,乃一憾事。
火鳥download欣賞 最後一首 firebird bercuese and finale
二十七
華格納的“尼貝龍指環”套歌劇之管弦樂片斷,有些史氏所無招式:水銀瀉地,四管齊鳴,以高伴低,弦木伴銅,你問我答,不分彼此,千軍萬馬,一統天下。有興趣研究者宜自己去找“那裏是那裏”,此處恕不公開“謎底”。
二十八
史氏“春之祭”的管弦樂法,最特出的一招是把整個樂隊當作一件打擊樂器來使用。以此招表現原始、粗野,不可謂不成功。可是,這實在是險到極點,近乎旁門左道的招式,稍為拿捏不准,便會“未傷敵而先傷已”。後來一些無此功力又無此內涵的東施之輩,濫用此招,把樂壇弄得一片剌耳鬼叫之聲,想這並不是史氏所樂於見到之事吧?
二十九
“用非管弦樂語言寫管弦樂樂曲”,例子可舉舒伯特為“露莎孟德”所寫的芭蕾音樂。雖然該曲充滿旋律美,句句可唱,但是,缺少對位,缺少戲劇性,缺少強烈的色彩變化和織體變化,從頭至尾只是旋律加伴奏,而且主要旋律都是頗為呆板的歌謠式節奏。以管弦樂曲論,這當然不算成功之作。請讀者勿誤會庸才阿鏜居然敢大貶天才舒伯特。以作品的充滿靈性、詩意、旋律和聲的美而自然、多變論,舒伯特是無人可及的。缺少第一流的對位技術而被公認為第一流作曲家,古今中外只有一位舒伯特。他三十一歲便英年早逝,可是給人類的音樂寶庫留下了多少無價珍寶!阿鏜對他連崇拜、欣賞、可惜都來不及,怎敢亂貶?怎忍亂貶?想指出的僅是:如缺少足夠的技藝與功力(包括對所寫之形式的瞭解和掌握),天才如舒伯特也會有不成功之作。凡夫俗子如我輩,欲寫好一曲半曲,能馬虎乎?能偷懶乎?能騙人乎?
三十
欣賞音樂難不難?說不難,何以鐘子期一死,俞伯牙便從此不再撫琴?可見知音不易得,賞樂相當難。說難,則何以除聾啞之人,生平不喜歡任何音樂,不曾自己哼唱過幾句的人幾乎找不到?可見音樂人人都能賞,絕非貴族之專利品。結論是:不同的人欣賞不同的音樂,不同的音樂需要不同的人來欣賞。欲賞樂者,不能不先弄清楚,自己是何種人,宜賞何種樂;欲人賞樂者,也要先弄清楚,自己有的是何種音樂,需要何種人才宜欣賞。如此,則不會有人埋怨欲賞無樂,有人埋怨有樂無人賞。
三十一
所謂“”知音難求,是指確實優秀,卻尚無人知的作家作品,不易遇到能賞識的人。時至今日,誰不會說“巴赫偉大”、“我喜歡貝多芬”?可是,偉大的巴哈去世後,整整一百年默默無聞,直到孟德爾松歷盡艱辛,把他的“馬太受難樂”排演出來後,世人才知道有巴哈。如問巴哈的在天之靈:“千萬世人尊稱您為音樂之父,究竟誰是你的真正知音?”大概巴哈會毫不考慮地答:“孟德爾松!”
三十二
賞樂如賞詩、賞畫,以“耐”字為高。詩要耐吟、畫要耐看、樂要耐聽。把柴可夫斯基和西貝柳斯的小提琴協奏曲相比較,相信一般人初聽都會喜歡柴多於西。可是聽到十次二十次以上,情形就很可能反過來,品位較高者會覺得柴協“膩”,西協卻越聽越有味。以此斷高下,自然是西高於柴。
三十三
如追根究底下去,是什麼因素造成一件作品“耐”或“不耐”?這是極難答的問題。就音樂來說,一般情形是厚重、含蓄,抒內心之情的作品比輕巧、華麗,描寫外界景物的作品耐聽;對位元豐富的作品比對位元貧乏的作品耐聽。但也不儘然。莫札特的作品並不厚重,舒伯特的作品對位元並不豐富,史特拉文斯基的作品以描寫外界景物的居多,但都很耐聽。無可爭議的是:情深情真的作品一定比情淺情假的作品耐聽。
三十四
中國傳統音樂與西方古典音樂的同異之處何在?同者,都講求好聽、高雅、有意境。異者,一、中樂音階一般是五至九聲,西樂音階是七至十二聲。三、中樂一般不轉調,西樂大量轉調。四、中樂器高音強低音弱,各種樂器的音色不易溶為一團,西樂器高中低音較平衡,大多數樂器的音色可溶為一體。五、中樂創作的思維一般是“砌磚式”,即越加越高,越加越長;西樂創作思維一般是“細胞分裂式”,即越變越多,越變越長。由此看來,西方古典音樂是已高而不易再高,中國傳統音樂是不高而大有機會再高。
三十七
論音樂充滿剛陽氣,古今中外,無人可與貝多芬相比。貝多芬的作品,充滿力感,永遠激勵人向上。有句話說:“學琴的孩子不會變壞”,也許還可以這麼說:“愛聽貝多芬音樂的人不會頹唐不振。”
三十八
每次聽貝多芬第九交響樂第四樂章,都有把靈魂清洗了一遍和跟最好的老師上了一堂作曲課的感覺。這真是一首神聖、神奇、集大成的至尊之作——一般人都能接受和喜歡它簡單、易唱、好聽的主題旋律;行家不能不佩服它極其高明的作曲技巧;政治家可從中體會出人類最崇高、最終極的政治理念;宗教家會認同其眾生平等,人類互愛,神偉大,人渺小的精神;哲學家會發現它用最抽象而直接的語言,把他們用長篇大論都講不清楚的意思和道理,全明明白白地講了出來;建築師和數學家會驚歎其總體結構的龐大精妙,每一個組成部分都互相關聯而經得起嚴格分析、計算;文人雅士可從中引發諸多聯想甚至由此產生新的創作靈感......假如世界上只准留下一首樂曲,其他統統不准存在(當然包括筆者敝帚自珍的數十首小作品在內),別無選擇,我只好略帶痛苦地把這一票投給貝多芬這首“歡樂頌”。
三十九
選詞作曲——詞長不如詞短,情短不如情長。
四十
賞樂三部曲——一、多聽,二、多聽,三、還是多聽。多聽自能出味道,多聽自能辨高低,多聽自然成樂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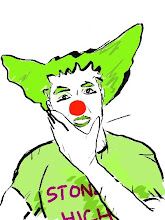

<< Home